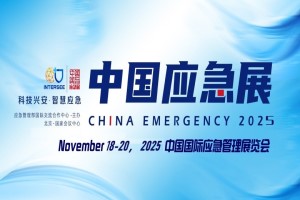白露谷
霜降豆
花生收在秋分后
白露一到,田里又开始忙了。
芒种前,我们在山下开了大概1分的地。花了1天的时间,集体出动仔细把地翻了一遍。又向人家讨了苗和种子,连带买的葱一起种了下去。还特别请了熟悉的老乡在旁边指导,一粒一粒的仔细播种,也有模有样的在菜苗边打了方格。干活时大家谈起了种地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最好的也只帮家里干过一些,但对于详细的做法没有人了解,完全凭感觉。



感觉总是美好的,坐在田边不由得开始畅想秋天的丰收,吃着自己种下的瓜菜心里美滋滋的。
日子一天天过,起初隔一周就会去田里看看,眼见苗长大了些心里也就放心了。
没过多久,一场大雨后地里积了水,一些苗淹到了。
立夏后,眼见野草长过了庄稼,除草时却分不清是草是苗。
进了伏天,天旱了起来,本来不多的苗更加稀疏。想着要不要补种,不想,第二天又开始连着下雨,地里起泥。
立秋了想着赶在最后买了肥料准备再挽救一下,等到了田里一看几乎全军覆没。拿着肥料大家互相看看了又都走了,不如把肥留下来,等着明年再来吧!
白露到了,地还是那么荒,像未开前一样。唯独几株葱退出去了刚种时的翠绿,枯黄的叶子,开败的葱花,像几个饱经风雨的老人,佝偻着眼巴巴地看着那片地。



中秋节前,我们来到驻村工作点入户开展节前慰问。
下沟村在册127户256人,常住在村32户55人,最年轻的是村里的书记55岁。
值得一提的是村里还有个地方名叫“小台湾”是村头处的一块土塬,因一条沟将它与村本部分隔开了就得了个“小台湾”的戏称。“小台湾”上原来也有十几户人家,但现在常在的只剩下了一户、二人和一条狗守着这一方宝岛。
村里人少但地却不荒,庄稼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多少都要种着。哪怕是70岁的老人也不闲着,在屋前屋后开块小地种点瓜菜。
进了屋总会问,“伯伯,你家里种着多少亩地呀?种的啥呀?一亩出多少斤?收入还行吧”“地就种1亩多,种点莜面,大概出个200来斤也不卖就自己用了”“嗯,挺好的”。

出了屋子细想一下,一亩地到底有多大?莜麦长什么样?
看见屋前的西红柿秧上硕果累累,还想请教,“伯伯,这地怎么种的这么好?可以教教我们?”“没怎么样,浇点水就行了。这有啥好学的,年轻人不用干这。”
每次到村里都是热热闹闹走上一圈,回来路上心里空空如也。
仔细想想同样是地,也是春天播种等着秋天收获,浇水、施肥一样不少为什么还是没有收成?
因为我们越走越远,并不理解农村。
70后总会回忆在村里一天放羊要走多少里路,种地点豆一天能有多少颗;
80后想总会想起放“麦假”两只胳膊上被麦秆划的密密麻麻;
90后总会想起奶奶家的西红柿很好吃;
再往后想起农村还会有什么?农家乐、农家采摘..........
农民世代在土地上生产生活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态。二十四节气就是很好的例子,脱离农耕的二十四节气让我们理解的就只剩下朋友圈里赏心悦目的海报、鸡汤式的文案以及养生小知识。在发展中文化变迁与人口流动都是必然,而过程中总有一些留下的人和物,他们当然不是时代的主角但正是他们在守着“乡愁”。

晏阳初曾说“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因为这一块没有收成的地,当我们再看到“粮食再获丰收”“秋粮再创新高”的新闻时,一串串数字就不仅是数字,还是透过屏幕与报纸的阵阵麦香,以及播种者的喜悦!
中国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从理解“三农”开始!
来源:青春崇礼